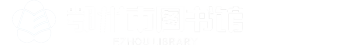2006年第01期(总第092期)
《行政强制法》向建成“法治政府”迈出重要一步
每逢年终岁尾,在全国人在常委会是后一次会议上,总有一些开始审议的法律草案成为热点--2004年底是《反分裂国国家法(草案)》,2005年底则是《行政强制法(草案)》。
2005年12月24日,这部重在规范政府强制行为的法律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果一切顺利,有望在数月之后获正式通过。
1996年遏制“乱处罚”的《行政处罚法》实施,2003年针对“乱审批”的《行政许可法》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行政强制法》可谓是政府行政权力10年来的第三次“缩水”,也显示中国向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再迈进了一步。
“力求将公民的损失降到最小”
《行政强制法》的核心,“最重要的就是程序化。”中国政治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刚凌说。
例如,草案对“限制公民人身**”和“进入公民住宅”这样的强制措施规定了特别的严格程序--进入公民住宅实施强制措施,必须出示县级以上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书,对人身**当场进行强制措施,必须立即告诉家属和有关单位实施的机关和实施地点;在紧急情况下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进入公民住宅,限制公民检身**的,应当在返回行政机关后6小时内补办手续。
全国人大的资料显示,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有48部法律和72部法规对各种行政强制措施作出了规定,其名称多达200多种。“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一些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既存在对某些严重违法行为缺乏强制手段处理不力的情况,也存在行政强制手段滥用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做草案说明时说。
“行政强制在实践当中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公民不履行法定义务,没有行政强制手段不利于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管理。但从另一方面看,行政强制如果运用不当,就很容易伤害公民的权利。”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说。
对于这一对矛盾,应松年认为,“按照法治政府的原则,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要由法定机关实施并力求将公民的损失降到最小。”
长期以来,包括强制拆迁等行政强制权力,多有未经法律授权者,其越权行政带问题,正是近年民众上访反映的焦点之一。
为此,草案规定了行政强制的四大原则:法定原则,即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任何机关和组织不得实施行政强制;适当原则,即选择适当的行政强制方式,最小限度损害当事人权益;不得滥用原则,即可以不用时,不得使用行政强制措施;和解原则,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与当事人达成和解。
以上种种,都是草案的亮点与新意,其立法目的清晰地指向和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草案仍有不足。“尤其是,在行政强制权力配置方面基本维持了现状,而更加合理性的变化并不明显。”薛刚凌说。
关于行政强制权力配置方面的争议,在草案形成过程中一直存在。应松年教授一直建议:根据裁执分离的原则,可以考虑在行政机关内专设执行机构(如在司法部或财政部下专设执行署),而由法院专司裁决。这样做,既可以使行政权力机关需要强制执行时,多一层监督避免出错而侵犯公民权利,又可将一切行政强制措施由法院裁决,以保持公正,也有助于减轻当前“执行难”的困扰。这一建议目前尚未获得立法部门回应。
行政法典出台已进入视野
“上述三大行政单行法出台之后,大部分行政权力都已被内入法律框架,制订并出台统一的行政基本法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担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会长的应松年和该会执行会长姜明安对本刊说。这部“行政基本法”,就是各界翘首以盼的《行政程序法》。该法最终分布行将标志着中国行政法体系的基本完善,也是“法治政府”能否建成的重要标志。
“有媒体报道说,《行政强制法》是行政立法三大步的最后一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尚未出台的《行政程序法》才是所有行政单行法的法典。”
中国行政法体系的建设,选择了从单行法到基本法的立法路径。一些学者认为,从单行法逐个推进,令很多案例的法律标准不一,同时也抬高了立法成本。
应松年教授参与起草了每一部行政单行法。他回忆,当初并非不想提前制定《行政程序法》,而是因为“时机不成熟”。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这是中国首部行政单行法,使得“民告官”“行政程序须合法”等理论落实到法律层面并渐入人心。此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要不要搞一部《行政程序法》。”应松年说,“环顾周边,《行政程序法》都是各国行政法律的核心。”但当时在国内,包括决策层和民众普遍重实体而轻程序。
在这样的氛围中,“于是干脆化整为零,先把对市场经济影响最大的几个行为单独列出来,把它们的程序问题先解决,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和行政收费,四个单行法。”应松年说。
2001年12月27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长李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的法制讲座上要求“进一步加快行政立法的进程,在抓紧制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措施法》《行政收费法》等法律的同时,着手研究制定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而这一系列法律的制定,都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90年代初,对市场经济曩最大的是行政处罚,所以我们第一个选择的是《行政处罚法》。”应松年说。
而2003年出台的《行政许可法》则与当时要求减少行政审批,遏制政府和官员滥用权力的强烈呼声有关。
接下来的《行政收费法》,原本与《行政强制法》一道,业已进入十届全国人大的一类立法规划序列(即如无特殊情况,2008年本届人大结束之前需要完成的立法)。但据本刊了解,《行政许可法》的第五章专门就收费问题进行了一些规定,并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效果,使得《行政收费法》的制定变得不很迫切。全国人**制工作委员会下设的行政法起草小组迄今尚未起草《行政收费法》。这也意味着,规划中的四大行政单行法实际上已缩减为三部,《行政强制法》也就成为了行政法典出台前的最后一大步。
目前,《行政程序法(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工委。在学界普遍认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时机已经成熟之际,十届全国人大是否会在余下的两年届期内通过这部法律?
“现在无法给出确切的答复,”全国人**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说,“在立法问题上,有些事情非常复杂,学理只是其中一方面。”
“即使本届人大没有政法法典,下届人大也要通过,否则本届政府于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的‘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就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姜明安说。
建筑设计师为中国正出现“千城一面”危机而揪心
大广场、宽马路、大草坪、豪华办公楼、欧化建筑,近年来一些城市大兴土木所树立的城市形象已引起中国建筑设计师和政府官员的批评和忧虑。他们认为,片面的求变、求洋、求大心态,使一些历史名城风貌荡然无存,中国正遭遇“千城一面”的建筑特色危机。
就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如火如荼时,中国建筑业也进入鼎盛时期。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当前的房屋建设规模堪称世界第一,有四百亿平方米左右,中国每年建成的房屋面积已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一年建成建筑面积的总和。预测到2010年中国房屋总建筑面积将达到519亿平方米。
广州设计院副院长、总建筑师郭明卓批评道,“近年中国的住宅设计已成为一种流行艺术。媚俗、跟风、抄袭、追求时尚使建筑形式变化之快,差不多赶上时装的流行周期。一年一个口味,去年欧陆式,今年现代化。可以说,建筑在住宅方面已经变成了流行的艺术。建筑形式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速度不是半年、一年、两年,而是一个时代。”
他说,罗马的斗兽场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北京紫禁城的一个角楼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仍然为人们所喜爱。好的建筑就像古典音乐,其艺术价值是永恒的。
而建筑设计师的忧虑不只是中国很多城市建筑形式和风格的雷同,更指责一些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以致中国一些城市成了“标新立异”建筑设计的“实验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总工程师江欢成说,最近南方某地一座高塔评出了三个设计方案,其中一个设计方案有如仙女扭腰,扭而略倾,倾斜电梯。而这个不可实施的方案竟被专家评出并打算作为最后的实施方案。
江欢成说,用不合理的结构来获得“视角冲击”目前在中国建筑界已经成为时尚。建筑物的忌讳是大悬挑、高重心、偏斜扭转。而恰恰就是这些,当今大行其道。其结果必然是拼材料,耗费几倍于合理的用量,效率低,隐患多。建筑应坚持“坚固、实用、经济、美观”,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怪为美,以不合理为美。
中国建筑设计大师郭明卓认为,业主和政府官员总是要求建筑师做“标志性建筑”,而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都是标志性建筑,城市景观将杂乱无章。标志性建筑物是城市建设的亮点,但整个城市形象的提升,不是单靠几个标志性建筑就可以满足